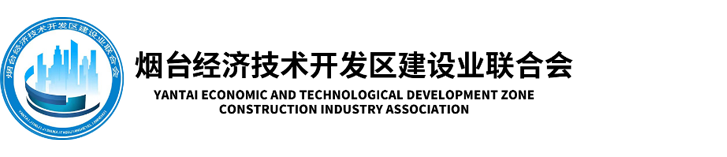北京市建筑設計研究院顧問總建筑師劉力
獲第六屆梁思成建筑獎
代表作有北京炎黃藝術館、北京動物園大熊貓館、北京圖書大廈、北京恒基中心等。
文明與現代的西單文化廣場
曾是建國五十周年大慶的工程之一的 20 世紀的完美場所,讓每個人都感悟著它的魅力,讓每個商家都感覺著它的力量;長安街上唯一的大型綠地廣場和集購物、康體、娛樂、休閑為一體的多元化商業地帶,以它獨有的氣質吸引著國內外的企業和人們。
總占地面積 15000 平方米,總建筑面積 39990 平方米。南倚長安街與時代廣場遙遙相望;北與中友百貨一脈相連;東臨聞名遐邇的圖書大廈,西望絕佳建筑特色的中銀大廈。平視它,綠色的草坪、整齊的便道,以及彩亮的場燈,勾畫著一幅簡明和清晰的廣場效果;俯視它,舞臺、雕塑、圓盤、道路,組合出一幅休閑的風景之圖。
·位于西單路口東北方向; ·項目總建筑面積3.5萬多平方米;
·其中廣場占地1.5萬平方米; ·工程總投資5.4億元;
·廣場中央高13米,直徑7 米的超白鋼化玻璃錐是廣場的標志性建筑
·廣場東北部為坡式綠地。 ·分地上、地下兩層;
·棋盤式綠地廣場南部和西部,為棋盤線的紅、黃、灰三色廣場磚甬道,與甬道兩側的黑白點……
唐宋時期的建筑風格
炎黃藝術館 是藝術大師黃胄創建的我國第一座民辦公助大型藝術館。旨在收藏和展覽中華民族優秀文化藝術品,為海內外藝術家、收藏家提供藝術交流的場地。該館以收藏、研究、展示當代中國畫為主,兼顧中國古代字畫及文物文獻和其他藝術作品的收藏與研究,以期推動中國畫和民族美術事業的繁榮發展。黃胄先生為藝術館捐贈自己的大量珍貴收藏和作品,許多藝術家為藝術館捐贈自己的優秀作品。
藝術館的建筑造型吸取了唐宋時期的建筑風格,并采取非對稱格局,集時代精神、文化傳統與地方特色于一體。屋頂采用門頭溝茄皮紫色琉璃瓦,檐口瓦當飾以“炎黃”二字圖形紋樣,外墻以北京西山民居常用的青石板貼面,基座正門側壁均為以蘆溝橋的蘑菇石砌成。藝術館的設計工程由北京建筑設計院副總設計師劉力主持。
藝術館的正門是兵器部7312廠用發炮彈殼熔鑄而成的大銅門,上鐫有“說唱俑”、“唐三彩”、“簪花仕女”等古代藝術珍品的圖案浮雕。小展廳和底層入口處的兩堂銅門為臺灣文化界企業界人士捐贈,圖案是“吉祥雙鳳”與“和氏璧”。
藝術館一期主體建筑地上二層半,地下一層半。內設展廳、多功能廳、理事廳、畫庫、畫室、裝裱修復車間、畫廊、工藝美術商店、炎黃藝術國際交流聯誼會、攝影室等。展廳九個,空間構成采用簇集組織,分合自如,最大限度采用自然光,又避免陽光對展品的直射,展柜內均采用冷光源燈、防火防盜、恒溫恒濕、空調通風及背景音樂等設施,解決了藝術品與欣賞者的雙重需要。多功能廳集展廳、會議廳、電教廳于一身,采光、音響設施齊全。畫庫結構堅固,擁有完善的恒溫、恒濕、空調通風、防火防盜、防蟲防微生物的設施。
周總理指示“蓋個最大的書店”
總建筑面積5萬余平方米。10萬種圖書都已上架。在營業大廳中,新穎獨特的設計令人耳目一新。書架全部采用弧形設計制作,呈放射狀排列,在中央共享空間,大型不銹鋼圓錐將四層銷售大廳連成有機整體,制作精細、氣勢磅礴的雕塑坐落其中。大廳西側,表現中華民族文明古國的四大發明浮雕壁畫與大型圓雕交相輝映。
北京之北,亞運村安立路和惠忠路交叉口附近,一座形似金字塔的暗色建筑隱在四周的樓群中,古樸大氣,卻并不張揚。
這不是金字塔,它的設計靈感也和金字塔無關。事實上,這座建筑的主題是“斗”———中國傳統的容器,扣在一萬多平方米的建筑面積上,營造出一個傳統與現代相結合的藝術空間。這是北京炎黃藝術館,劉力喜歡稱它為“大屋頂”。
“大屋頂”是和另外兩個方案一起,由劉力提交給藝術館的主人、著名畫家黃胄先生的。1986年,炎黃藝術館開始籌建,作為我國第一座民辦公助的大型藝術館,黃胄的理想是把它建成高品位的藝術展覽、交流場所,體現中華民族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公益藝術館。“我這個藝術館本身也要是展品。”黃胄這樣告訴負責設計藝術館的建筑師劉力。
藝術家傾注了大量心血,建筑師也不敢怠慢。劉力說自己在和黃胄反復探討設計方案的過程中,領悟了不少新鮮的藝術理念。既要傳統,又要現代,如何落實到具體的建筑中去?當時北京建筑界提倡“古都風貌”,在這個時代背景下,劉力覺得,保留傳統元素固然是個趨勢,但不像移植一些傳統符號那么簡單。“建筑給人的感受,不完全是看到一個什么符號,就想到了中國人的老祖宗。”劉力說,“我在想怎么能夠把東方文化的那種‘基因’給挖掘出來。”這里很重要的一個命題就是“空間組織”,劉力提到當時看過的一本分析中國建筑特點的書,臺灣人寫的《華夏意匠》,書里講到故宮等古建筑喜歡運用的“穿堂而過”等形式,體現出豐富多元的建筑精神,而不是簡單搬用某些元件。劉力仿佛找到了解決問題的某種暗示。當從形式上難以突破時,思考如何組織空間,可能是更接近建筑本質的思路。
“建筑師不是雕塑家”
北京動物園大熊貓館
建筑師不是雕塑家,視覺效果對于建筑來說雖然重要,可不是最重要的。建筑師營造的是一種環境,人能夠進入,并且參與其中的環境。這個環境造好了,建筑才算成功。比方說國家大劇院,外表看挺寧靜的,走進去發現,里邊的環境讓人振奮,這感覺就很好。可是現在很多業主就是看外表,誘導我們的建筑師們也只重視外表,很多年輕同志,這個建筑的功能、體量還沒搞清楚呢,創意就滿天飛。
當初設計炎黃藝術館時,就有很多反對意見,說我們這個檐口如何如何,屋脊如何如何,底下的斗拱如何如何,都是具象的意見,我和黃胄都沒有采納,堅持做我們認準的東西。因為你要是退了一步,就會步步后退。比如有人說屋頂不能是直的,要起翹;你起了翹之后,這個脊又不對了,還要做仙人走獸;做了仙人走獸,別的也都得做,就陷入模仿的泥沼了。
戴念慈先生給我們評過炎黃藝術館這個圖,他對我在東邊做的那兩個垂直的樓梯很欣賞,說這東西可以。因為在西方,現代建筑對人的交通動線的情態比較重視,公共空間的設計應該清晰合理,人進入建筑就知道怎么走。可是現在很多建筑就像迷魂陣,我在做商業公共建筑時,主要的工作就是處理行動空間。
北京動物園原來那個老熊貓館不好,雙坡頂,開小窗,里頭擱倆熊貓,像個托兒所一樣。我戴紅領巾的時候就去看過,后來我兒子戴紅領巾的時候我又帶他去看,我覺得這不是熊貓的天地,是小孩兒的天地。所以后來設計新熊貓館時,我就特別注意,這是給熊貓住的房子,人是來參觀的。熊貓的生活環境必須設計好,外邊還有運動場,讓熊貓生活得很舒服,在不經意中被游客欣賞。游客的交通動線要流暢,走著走著就到室外了,走著走著又會上房頂了,形成引導效果。人和動物要盡量親近,還得保證安全。熊貓館里的玻璃做得很大,我為此找過秦皇島的一位玻璃研究專家,他專門研究軍用殲擊機的機艙玻璃。這種玻璃用在熊貓館里,經得住熊貓發情時使勁拍打。
熊貓館的外形是渾圓的,勾勒出熊貓那種神態就行,可不能真弄個熊貓的形狀擱那兒。建筑的結構畢竟要實用,就得是抽象語言,不能寫實。北京東郊有個“福祿壽”的建筑,是個旅館,好家伙,就造成三個人站著,總統套間就是那人手里捧著的壽桃。這就太具象化了,失去了建筑的本來意義。
最新推薦
-
煙會開發區今年首宗“標準地”成功掛牌出讓
2021-04-302月23日,開發區2021年第一宗標 準地"成功掛牌出讓。該地塊位于開發區 B-35小區,土地位置為臺北中路以東,揚 州大街以北,出讓面積為1...
-
瞠起眼來找漏洞重點領域循環査 --開發區開展建筑工地安全隱惠大排査行動
2021-04-30為進一歩補短板、強弱項、堵漏洞, 牢牢守住安全生產底線,煙臺開發區開展 了建筑施工領域安全風險隱患大排查大整 治行動月活動,他們...
-
開發區重點項目推進情況跟蹤報道
2021-04-30天馬相城四期 總建筑面積約41萬平方米,包括25棟住宅和1棟幼兒園。計劃年內完成10棟 高層主體施工,全部單體外墻(窗式幕墻)施工完成50%...